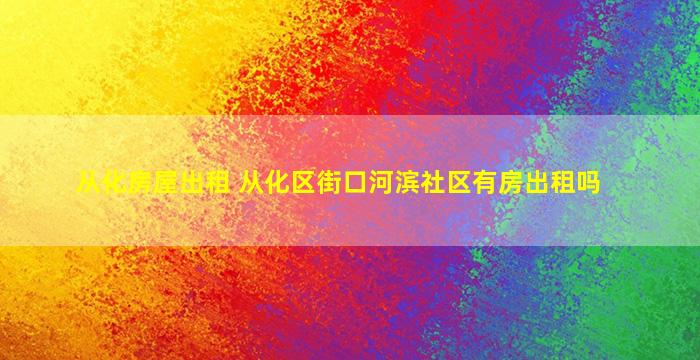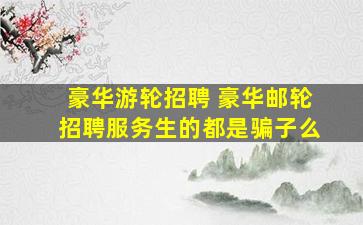傅总夫人又闹离婚了 厉总离婚请别怂
二婚妻子闹离婚老公不回家啥结局
然后你就闹离婚了老公不回家如果两个人还能和好的话那就赶紧回去上一步如果一直这样的话那就只能面临离婚的今晚恋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要互相信任,很多方面是要坦诚相告,但是每个人还是要有属于自己的空间,自己的世界,也会保留一些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隐私,是很正常的啦!要给对方一些空间,谈恋爱,就像放风筝,风筝想要飞的更搞更远,但是线依然牵在.老婆,丈夫对妻子的称呼,也指陪伴老公一起变老的女人。最初的含义是指老年的妇女。不同的人对老婆有不同的称呼,如古代皇帝称老婆叫梓童、宰相称老婆叫夫人等。后来王晋卿诗句有云:“老婆心急凭相劝”。这一“老婆”是指老是主持家务的妻子。因此,后来称呼自己的妻子叫“老婆”。另有同名歌曲及电影。感动和心动开始的。但是只有感动而没有彼此的欣赏仍成不了恋人;只有心动,没有持续的关心和责任,也只能收获短暂的爱情。真正的爱情始于感动或心动,但须以关心和责任为扶持,以欣赏和吸引为指路,才能最终走向婚姻的殿堂。
种下爱,收获爱。但需勤浇灌和培土。但如果一方种下的不是爱,那么无论如何也不会收获爱。托尔斯泰说过,感激不是爱。也许所有的爱情在结婚后都会演变成亲情,但它一开始绝不是亲情。
如果你找到的那个人因为一次小误会或小事故就离你而去,那么你不必后悔,因为这恰恰证明了你们的不适合,或者说你们还没有找到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就是能克服一切障碍,甚至勇于面对疾病和*亡的威胁。如果只是一个小小的误会就足以让你们分手,那么不如没有遗憾地放弃吧。
爱的路不会是一帆风顺。有时你爱的人不再爱你,有时你的爱渐渐冷漠,与是爱就到了终点,需要做出选择。爱就是在一段又一段路口走出无数次选择,你不知道要经过几重关口,但只要有耐心和勇气,最终都会找到自己的路。
爱情的路上有许多困惑,但真正的爱情是彼此欣赏,彼此包容对方、体谅对方,同时两个人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志向,只有这样,才能天长地久。真正的爱情是让人安心的,你不会要求他变得更好,因为在你眼里他已经足够好。如果他做出了改变,那也是他自愿做出的决定。
傅斯年的人物轶事
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特别重视史料的发掘。为此,傅斯年曾主持购进清代所藏内阁大库档案,费资不少,但在整理的过程中傅斯年却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静心斋对李济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却问:“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了大笑。
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并最终把孔轰下台。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难逃此数。傅斯年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下台——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历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自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了官费留学。从1919年至1926年,他先后留学英、德。留学期间,傅斯年一心扑在学习上。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忆赵家》中记录。当时的留学生大都“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就鼓励大家离婚,但这么多留学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来读书、心无旁骛不理会男女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以至于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在“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鹄”的世俗风气中,傅斯年连个硕士学位也没拿到。但是,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问渊博。
傅斯年先生疼爱学生是众所周知的。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猝*于*大学讲台,新闻报道曾广播说“傅斯年先生弃世”,被其学生听成了“傅斯年先生气*”。于是*大学学生聚众要求校方惩办凶手,直到当时*国民*官员出面解释清楚,学生才退去。由此可见傅斯年先生深受学生喜爱。
已逝傅斯年夫人俞大彩的回忆文章记道:“他常在中午返家时,偕我到各宿舍探视,并查看学生的伙食。他一进餐厅,男生必高呼欢迎校长,女生则拥到他身旁。他去世后,学生们痛哭哀悼,是青年们发乎自然的真情。”
*大学校史馆张小姐说:尽管傅校长执掌台大仅仅700余天,可台大人始终将他视为“台大的守护神”,安葬他骨灰的校内植物园被命名为“傅园”。大概在学者中间,傅斯年的体胖是有名的。一次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质量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这样的话真是能给肥胖的人壮气。
不过,关于傅斯年之胖的故事还属以下这则最为有趣。傅斯年、李济还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主人特别为他们三个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他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的时候,剩下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傅斯年比刚才的两个人都胖得多,于是两个工人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请客的主人甚是尴尬!我想许多人看到这里都会莞尔一笑,因为在四川抬滑竿的,实在没有太壮的人!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傅斯年的祖先傅以渐是清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其后,傅氏家族科考得意者不计其数,官至封疆大吏的也不乏其人。因此,山东傅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的称誉。但是到了傅斯年这一代,傅氏家学虽然依旧渊源,但已经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了。傅斯年在北大期间的生活费用,就是靠别人接济的。傅斯年的国学功底是非常深厚的,上大学时,虽然只有十几岁,但俨然一位“国学小专家”。他的治学功底甚至强过了北大当时的某些教授。据傅斯年好友罗家伦回忆,“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傅斯年本是黄侃的得意弟子,但一次偶然机缘,傅斯年竟“背叛”师门,成了胡适的学生。胡适刚到北大教授*哲学史的时候,因为讲授方法和内容特别,在学生中引起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胡适远不如国学大师陈汉章,想把他赶走;有人则认为,胡适读的书虽然没有陈汉章多,讲课却颇有新意。傅斯年本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在同室顾颉刚的鼓动下去旁听了几次胡适的课。结果听完之后非常满意,于是傅斯年对哲学系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由于傅斯年在同学中的威信,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站稳了脚跟。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胡适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参政而不从政
他在担任国民参政员时,曾经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为保护孔祥熙,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想为孔祥熙说情。二人有这样一段著名的对话。
蒋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无奈,只得让孔祥熙下台。
1945年6月,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对宋子文的胡作非为进行了猛烈抨击。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在社会上的一片反对声中辞职。也许是听腻了阿谀奉承的话,看腻了唯唯诺诺之态,*对傅斯年这个桀骜不驯之士不但没有恼怒,反而欣赏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当官。
早在1946年初,*就与陈布雷商量,要在北方人士中补充一个国府委员。陈布雷对*说,北方不容易找到合适人选,*提议说:“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说:“他怕不干吧。”*大概不相信有人不愿当官,他很有信心地说:“大家劝他。”
结果,任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两人一旦加入*,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一入*,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
对于傅斯年拒不做官的气节,李敖一直赞誉有加。在《李敖有话说》中他就说:“有一个学生领袖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他不但不加入国民*,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吃掉,不被国民*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也不做*,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到*后,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到总统府吃饭,商议国事。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到*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的地位。”
遗憾的是,这位敢说话、办实事的台大校长,来*不到一年,就在参加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时突然倒在了议会厅。*闻讯后,立即派行政院长陈诚前去指挥抢救,动员*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他本人则守候在电话旁,焦急等待陈诚每半小时的汇报。傅斯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仅55岁。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由蒋梦麟召集的“农复会”一次会议,讨论农业教育改进和保送台大学生出国深造问题。在这个会上,傅提了不少意见,据在现场的人回忆说,他一会儿用汉语讲话,一会儿用英语和美国人交谈,一会儿汉英交杂,滔滔不绝地大发宏论。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他讲的话比任何人都多。午饭后稍事休息,傅又于下午2时许赶往省议会厅,列席*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这一天,参议会上所质询的问题全是有关教育行政方面的事务。下午会议开始后,傅斯年登台讲话,但主要由时任*省教育厅厅长的陈雪屏作答。到了5点40分左右,参议员郭国基突然蹦将起来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
这郭国基乃*省屏东人,生于1900年,曾留学日本。此人好勇斗狠,一生的理想追求就是造反起事,占山为王,或先把天下搞乱,然后再由他出面来个“天下大治”等。在日本留学时,郭氏就开始率领李铁拐、张歪嘴、王拴狗等一帮乌合之众与流氓无产者,打起“苍天已*,国基当立”的大旗或明或暗地闹将起来。抗战胜利后,他对国民*派员接收*极不甘心,再度以流氓无产者的姿态和当地码头黑老大的形象,纠集蒋渭川、王添灯等一批流氓恶棍加日治时期豢养的汉*走狗,与以国民*接收大员陈仪为代表的*省行政公署长官公开叫起板来,对大陆赴*政官员极尽丑化、*蔑之能事。未久,郭又鲤鱼跳龙门,一跃成为*省参议会的议员和立法委员。坐上*大员专用木头皮椅的郭氏,大有小人得志的做派,无论在什么场合,总是难以收敛流氓无产者的本性,胡乱发一些聪明中伴着糊涂、道理中伴着歪理邪说并散发着烧杀劫掠火*味甚浓的长篇宏论,气焰凶妄,举止轻狂,江湖上人送外号“郭大炮”。
意想不到的是,作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竟与这样一个流氓恶棍在议会大厅遭遇了。
当时的*大学属*省*拨款,故“郭大炮”便以地头蛇身份,怪叫着向“傅大炮”开起火来。据在场者事后透露,郭的发难主要是国民*教育部从大陆抢运来台并存放于*大学的器材如何处理,以及放宽台大招生尺度等问题。此事看起来简单,而又十分敏感、复杂、棘手。如台大之招生,尺度已尽量放宽,招生人数已达最大限度,但各界仍不满意,特别是郭国基辈纠集部分失意政客,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向学校施加压力,惹得傅氏极其恼火愤怒。今日郭氏之质询,当然需由傅斯年亲自答复,于是傅不得不第二次登台讲话。在回答完上述两个问题之后,郭又提出*大学用的是*人的钱,就应该多聘台籍教授,多取*土著学生,否则便是与台籍人民作对云云。傅针对郭的无知狂妄,开始予以反击,在讲台上大谈其办学的原则、规矩、计划与理想等,并称台大考试对台籍学生已尽量照顾,考虑到台籍学生的国语水平较差,光复未久,在录取时专门规定国文科分数比大陆学生降低10分录取等。讲着讲着情绪激动起来,傅说道:“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们摒弃于校门之外。”最后他高声说道:“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
讲完话时,大约是6时10分,傅斯年满含怨气地慢步走下讲坛。就在即将回到座位时,他突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坐在台下的陈雪屏见状,赶紧上前搀扶,傅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倒在陈雪屏怀中昏厥过去。离得较近的议员刘传来赶紧跑上前来,把傅斯年扶到列席人员的坐席上,让其躺下,顺便拿陈雪屏的皮包做了枕头。从此傅进入昏迷状态,再也没有醒来。
胡适为什么不敢与原配夫人离婚
胡适一家在美国纽约时,住的是五楼的公寓。有一天,胡适不在家,有贼从窗户里爬了进来,当时胡适的太太江冬秀正在做饭,突然看见了贼。她受到惊吓的同时,却并没有如美国女人面对歹徒时所习惯的大声尖叫,而是迅即走到大门口,拉开门,义正辞严地对贼说了一个英文单词:“GO!”她的大胆与果决吓住了贼,他竟然有些不知所措。也许在他的职业生涯里,从来没有遭遇过这样临危不惧的女人,而且还是个矮矮胖胖、面色慈祥、手无缚鸡之力的外国老太太。他愣在原地好一会儿,然后就真的顺着江冬秀的指示出去了。江冬秀关上房门,折回厨房,继续做她的饭。
1938年,胡适受命出任驻美大使。对此,江冬秀大加反对,写信痛责胡适。她从来不想做官太太,而只是希望胡适能够专注于学术。胡适写信给江冬秀解释:“我们徽州有句古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青山就是我们的*,我们今日所以能抬头见世人者,正是因为我们背上还有一个*的*在。我们做工,只是对这个*,这青山,出一点汗而已。”他在另一封信中,对妻子发愿说:“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
胡适出身于安徽望族,自小衣食无虑,且见识过欧美权贵的享受,但他仍然艰苦朴素。在担任驻美国大使期间,他无论是公款还是私款,能节约一分就节约一分。如出门公干,为了省下门前叫出租车要付的小费,他都是跑到大使馆门前大道的拐角处才叫出租车。江冬秀给他寄衣服,他写信回复:“一些衣服没舍得穿,还都很新,不要多寄了!”
1928年7月15日,胡适谈《贞*问题》:“女子为强暴所*,不必*。失身女子的贞*并没有损失。娶一个被*的女子,与娶一个‘处女’,究竟有何区别?若有人敢打破这种‘处女迷信’,我们应该敬重他。”
20世纪20年代,上海泥城桥开了一间叫“四而楼”的酒馆,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请教当时任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挨不住脸面,只好亲自前往四而楼小酌,寻机向主人探问究竟。主人说,楼名取自《三字经》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只不过图个一本万利的彩头。胡几欲晕倒。
胡适说自己在任驻美大使期间,收藏了很多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在这个收藏里,他有一个发现:在全世界*里,只有三个*是没有怕老婆的故事,一是德国,一是日本,一是俄国。所以他得到一个结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都是自由民主的*;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都是独裁的或极权的*。
1921年10月中旬的一天,胡适应邀与辜鸿铭一起吃饭。胡在当天日记中就此写道:“许久不见这位老怪物了。今夜他谈的话最多。他最喜欢说笑话,也有很滑稽可喜的……他说:俗话有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我替他续两句:孔教拜孔子,孔子要上吊。此指孔教会诸人。他虽崇拜孔子,却瞧不起孔教会中人,尤其陈焕章,说陈焕章当读作陈混账。”
胡适当年曾感慨:*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这句话后来被李敖盗用。
胡适著书,有始无终,他的《*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下半部付之阙如。黄侃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调侃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其意,问他何出此言?黄侃的回答颇为阴损:“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学生这才听明白他是讽*适的著作没有下部,遂传为笑谈。
胡适曾跟自己的原配夫人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举刀相向:“你要离婚可以,先杀了我和你的两个儿子!”自此,江冬秀成了传言中的河东狮,胡适成了怕老婆的典范。为此,胡适曾自嘲道:“怕老婆的国度,将是更民主的国度。”
胡适写过一首关于文字方面的白话打油诗:“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胡适不耐寂寞。他声称最重视学术,要“二十年不谈政治”,数年之间,即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或不赞成其办报,担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续”。胡适自己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胡适所著的《*哲学史大纲》,是*最早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书籍。书出来后,胡适特地送一本给章太炎,并在封面里写“太炎先生指谬”,署名“胡适敬赠”。其中“太炎”和“胡适”二词右边都加条黑线,表示是“人名”。然而,章太炎不懂新式标点符号的应用,所以看到自己名字旁的黑线,即骂说:“何物胡适!敢在我名上胡抹乱画!”继而发现“胡适”两字旁边也画一黑线,这才笑说:“他名字边也有线,就彼此抵消了。”
胡适本有二十年不从政的誓言,但抗战爆发后,胡毅然出阁做了*驻美大使。胡做大使书生气十足,不喜酬酢,偏爱闲谈。一天,胡看报,见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为国会议员,因是旧友,乃请他吃饭。此公也是书生气十足,见是*大使邀请,欣然接受,也不管这个大使是张三还是李四。席间,史密斯突然说:“多年前我认识一个*学者,他叫胡适,不知他现在何方?”
胡适受*之请出任驻美大使,消息传出,日本方面备感压力之大,有舆论建议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方可抵抗住胡适。此三人是鹤见枯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古。“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
20年代末,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校长,曾邀请途经青岛的胡适到青岛大学来讲演。不料轮船抵达后,却因风浪太大,无法靠岸。胡适只好发一电报,电文曰:“宛在水中央。”杨接到电报后,回电曰:“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胡适每到一地,似乎都喜欢到该地的窑子里看看。1922年,胡适到济南参加“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讨论新学制”会议。10月13日,这天傍晚,胡适去理发,看来他实在太困顿了,以至于理发的时候都睡着了。洗头发时,他叫师傅用冷水洗头,才得以清醒。这天晚上,邮局失火停电,大约无事可做吧,他在日记里这样写:“我就到济源里去看看济南的窑子是个什么样子。进去了三家,都是济南本地的,简陋得很;大都是两楼两底或三楼三底的房子,每家约二人至四人不等,今夜因电灯灭了,只点油灯,故更觉简陋。十时半回寓,早睡。”
胡适刚从海外归来时,被礼聘为北大教授,他的课堂里一时间听众如云。傅斯年的好友顾颉刚去听了一次,回来跟他说:“那个胡博士是真有学问,你也去听听吧!”傅斯年就真去听了,不仅听,还问,一问一答之间,胡适的汗就下来了。胡适后来坦白交代说:他当时就发现了,像傅斯年这样的学生,国学根底比他还深厚,所以他常常提心吊胆。
胡适和汤用彤闲谈,汤说:“我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胡适也笑着对他说:“我也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说完,两人相视大笑。
胡适应邀到某大学演讲,他引用孔子、孟子、*的话时,就在黑板上写着: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见解时,引得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1923年,胡适曾经为青年们拟定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把《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也列了进去。*对胡适说:“我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识浅陋,但说连国学的最低限度都没有,我不服!”
1910年3月22日,大雨滂沱。胡适和一帮朋友在妓院喝酒,大醉后雇一辆人力车回家。车夫乘他酒醉,顺手牵羊,剥了他的衣裳,偷了他的钱包,把他扔在雨里了事。
本文链接:http://www.hzrhc.com/html/87965750.html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